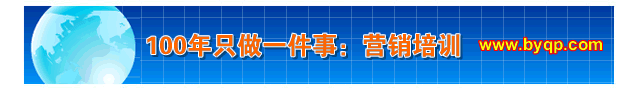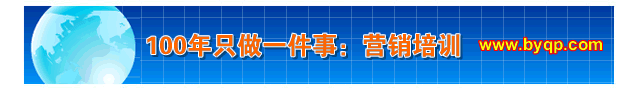二、过度表演
笔者了解到,在各地向旅游者开放的民俗风情村里,少数民族风俗舞台化的倾向十分明显。尽管表演者的行头比生活中真实的服饰漂亮百倍,但却缺少了该民族服饰原有的本真韵味,给人以虚假的感觉。发展乡村旅游项目,应避免为迎合游客好奇心和获取廉价收益,将一些民族民间神圣的“非常事项”日常化、表演化,最后造成乡土文化生态的异化和破坏。
欣赏和体验乡村的民风民俗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内容,而最能够体现民风民俗的莫过于乡村中的婚丧嫁娶、佳节祭奠这些标志性的事项。但是,村庄里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“非常事项”发生,也不是每天都有节日庆典等。这些“非常事项”遵循着乡村的时间节律、礼仪禁忌等,不能随便进行和改变,甚至不能示人。
“洞洞婚恋”本是贵州瑶族(青瑶)的一种恋爱习俗。姑娘14岁以后父母就让她单独住在一间小屋里,墙壁门上凿有一小洞,洞口正对着姑娘枕头。夜间,小伙子到自己爱慕的姑娘房门外,用根细棍通过恋爱洞把姑娘捅醒,隔门或隔墙谈心对歌,若谈得拢,可开门请进家,父母不干涉,家人还回避。谈不拢,姑娘可以装睡,小伙子便会知趣地离开,另找他人。当地俗话说:“一晚可以谈五个,终身只归一个人。”可见,瑶族虽然在婚恋选择上有较大的自由,恋爱方式也较为开放,但他们对婚姻问题却是非常严肃的。
当地一些旅游景点为了招揽生意,竟然打着展示民族婚俗旅游的名义搞不正当服务,最终激起了该民族的愤怒,他们对搞这种活动的旅游点发出警告:如果再不改,将派出“火枪队”武力解决。在上面案例中可以看到,在市场经济作用下,一些“非常事项”被日常化、表演化了。如云南、贵州、海南等一些民族村寨,几乎每天都向游客表演结婚仪式、神圣的祭祀舞蹈等。这些“非常事项”的日常化、表演化给当地乡村社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冲击,不是低廉的表演收入所能弥补的。
此外,大同小异的“竹竿舞”从海南的黎族跳到云南的傣族,从贵州的苗族跳到广西的侗族,被人笑称为少数民族民俗风情舞蹈表演的“跳竹竿”现象;“背新娘”在不少民俗村、民俗风情园甚至在毫不相干的溶洞景点内也比比皆是,挑逗诱骗游客上当,强行索要小费等不愉快的事件屡见报端;一些落后的东西如鬼文化、占卜文化等被刻意渲染,粗制滥造的鬼洞、鬼城、阴曹地府等品位庸俗低下;凡此种种,不亦而足。
像这样连少数民族的婚俗、宗教祭祀仪式都可以根据“旅游需求”随时随地“灵活”开展,那还有多少民俗文化的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呢?这种迁就游客“期望”的文化表演――同时也是文化歪曲对旅游接待地文化的自然发展极其有害,旅游者无法全面有效地接触和发现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,而是接受了一种经过了包装的“伪文化”、“伪民俗”,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会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。
三、过度管理
当国内一些企业摆脱艰难的“吃饭保命”的创业期后,逐步进入成长期。随着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加,管理层级的形成,企业的持续发展,必然会面对企业文化、组织结构、产权结构、经营战略转型等先天不足的因素。旅游企业老板的转型是痛苦的,但确是必须的。
其中,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,就是企业老板太忙了。太忙是表象,内在原因是啥呢?谭小芳老师认为是过度管理。该管的也许没管,不该管的一直在忙。谭小芳老师认为,如果老板要做大,首先应该更大气一些,完全可以相信自己员工的素质和对自身的控制力。以下谈几点个人看法:
1、授权管理
授权并不是弃权,而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好权力,也是为了更好的监控权力和掌控权力。
不必事必躬亲,事事不放心,其实绝大部分员工心中都有想干出一番事情的“理想”。最重要是对下属有授权要有明确的目标、要求和标准,这就够了。笔者在企业走访、咨询过程中,发现很多董事长做了总经理的工作;总经理做了经理的事情;经理做的很像业务员;业务员呢,都闲得很!我无意贬低我们的业务人员是多么的懒惰,也不想褒奖我们的营销经理是多么的勤快,在这里,我只想强调――角色定位决定工作方向,而工作方向决定工作方法。
2、树立榜样
不管是营销还是服务,企业各岗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它具有毛主席说的“播种机、宣传队、宣言书”似的效果,而且力量源源不断。没有人是想退步的,只要他觉得有希望且能实实在在的看到希望。具体方法可以设立高级职位,比如首席博客官、首席道歉官、首席市场官等等。
3、企业文化
从文化的层面对员工进行再宣贯,文化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,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谭老师认为,可以从员工工作的行为上着手,不断深化,由制度到行为,由行为到习惯,最终形成观念的革新和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可。此外,我发现企业还有很多过度效应的情况存在,比如:策划过度娱乐(公益缺失)、建设过度开发(环保缺失)、客户过度服务(隐私缺失),希望看过此文以后,各位企业家能在不平衡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平衡,走好经营的钢丝。
总之,治大国如烹小鲜――企业管理一定要适度,孔子云:过犹不及。过的害处还要大过不及。物极必反,过犹不及,管理者――切记切记!
<--pagelist end-->上一页 [1] [2]